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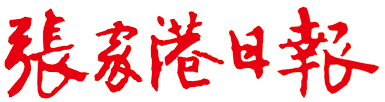
岁月深处的农村往事
□杨和生
在我上学的那些年,清晨常常在朦胧中被“哼哼哼”、“嗷嗷嗷”的一声声惊恐不安的猪叫声惊醒。这时家里的老人又说了,“作孽啊,猪又受惊吓了,又要几天不长膘了”!后来听大人说,这是给猪称重。
那时每到月初,队里就会安排四个壮汉,有拿大秤的,有拿粗毛竹棍、绳结的,从埭头开始,挨家挨户给每头猪称重。猪猪见自己窝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惊恐万状,在猪圈里乱窜。这时其中一个壮汉瞅准一头壮猪猛扑过去,抓住猪的两只耳朵,另一个壮汉扑上去揪住猪尾巴,一前一后把猪夹在中间,其余壮汉则用绳结套住猪身,再合力架到秤钩上,任凭猪四蹄乱蹬,“嗷嗷嗷”的惊叫声不绝于耳。司秤人报出称重数后马上有人记录。如有养羊的,同样如此。
当时农村流传这样的俗语,“农民不养猪,等吃西北风”,“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村养猪就成了头等大事。农民不但靠工分吃饭,更要靠多养猪多积肥才能多打粮,家庭生活也好得以改善。那时我家虽有弟妹六人,但劳力只有父母二人,单靠在队里挣工分是养活不了全家的。好在集体有规定,年终分配劳一半,肥一半,就是指挣工分与养猪积肥各半分配。于是父母平时把精力都放在养猪上。事实上,那时我家养猪在全队是比较出名的,不但猪养得多,而且养得也比一般人家要好。
每户农民积肥的依据,就是饲养生猪(含羊)常年产出大粪的质量、数量,以及每月累计称重的记录。每当集体庄稼需要施肥(施大粪)时,队长就会隔夜要求每家每户舀上一大桶粪送至集体库房,第二天队长就安排两个劳力负责取样。负责取样的人用一尺多长的粪标插进粪桶看刻度,度数越高说明大粪质量越好,反之则越差。数量主要是论每户出粪的担数。养猪多的人家,一只粪坑的粪就有六七十担之多。
余洪敏曾在某短视频中说小时候扫过猪圈,其实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在父母出早工后,上学前的第一要务就是打扫猪圈。先提上一桶水放在猪栏边,人跨过猪栏后,脚踩在用砖铺设的猪舍内,拿上一把专用木杷,把散在猪圈里的猪粪一耙耙推入粪池,再用竹扫把一边打扫,一边用清水清洗,这样猪圈既干净卫生,夏天还可减少蚊虫袭扰。下午放学回家后,仍然是围着猪转,不是挑猪草,就是到河边洗上几大篮子猪草,猪草沥干水后再全部切碎倒入大铁锅,然后搭配米糠、麸皮、稻草糠和少量麦粞等一起加水煮熟。这粗细搭配的一大铁锅猪饲料要确保猪一天的喂养。
到了冬天,为防止猪冻伤,每天要给猪窝换上一堆晒干的稻草,再把猪窝里被猪尿泡湿的稻草捧到场地上晒干,这样循环往复,天天如此。
成家后自己养了一头猪,也是我平生饲养的唯一一头生猪。听老人讲,猪长得个头大与快,品种很重要。比较理想的是那种腰身长、肩胛宽的猪仔。听说南通那边猪仔好,价钱也便宜,于是与老伴骑自行车再坐渡轮过去。那时的渡轮很小,渡轮顶层载牲畜、货物,渡轮底舱能载上三四十人。
“呜呜呜……”几声汽笛后,渡轮开始返程靠岸,工作人员搬出一块跳板架在渡轮与江岸之间。这跳板窄窄的,有六七米长,人走在跳板上颤颤巍巍的。就在小心翼翼之时,我的猪仔突然从未放稳的猪笼中窜了出来,“腾腾腾”直朝长江冲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猛地抓住巳窜到江边的猪仔,众多旅客为我的身手敏捷纷纷叫好。望着眼前滔滔不绝的长江,看看还在“嗷嗷”叫的猪仔,想到刚才的惊险一幕,我与老伴庆幸的同时,也不由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时光荏苒,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农村传统的养猪场景早已不见,但每每想起当年养猪的那些事,“哼哼哼”的猪叫声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响起……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