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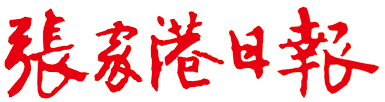
从“跋”中溯源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感
□王 娟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读了好几遍,每一次阅读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一次我抛弃了传统阅读方式,不再按照目录从头到尾阅读,而是选择先读完《从山峦到海洋》(跋)之后再阅读文章,这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让我仿佛打开了新的大门,收获颇丰。
正如文中所述“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所有的作品诞生都是这样,在顺畅地完成写作之前,一开始需要留心关注写作对象,做好各方面的积累,等到恰当的时间,这种写作冲动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文中所说“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这片“泥土”就是迟子建出生和长大的那片黑土地,那颗种子就是鄂温克族画家柳芭的母亲因腰伤从猎民点下山住进医院,“我”去医院探望她。这次探望让“我”看到了“这些少数民族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那一刻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对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便是“催生这部长篇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初稿完成后,依然需要打磨,中国海洋大学的写作环境赋予了作者宽容的心态和收敛的诗情,也让她对笔下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再次修改,不再苛责曾经的过往,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添加了虚构,进行了再创造。她也将喜欢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融进了作品中,这才有了如音乐般的四章《清晨》《正午》《黄昏》《尾声》,故事的主题便是由这四章内容展开。然而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回到现实,由九十岁的“我”来讲述现实中的人和事,用一句“来听我的故事吧”“接着听这个故事吧”“我愿意把余下的故事继续说给它们”,然后迅速进入回忆之中,以时间为经,故事发展为维,现实和回忆在不断交织,将故事向前推进。
迟子建是个智慧的作家,她并没有将已逝的鄂温克族画家柳芭作为主要人物,而是将她的外祖母作为中心人物,通过外祖母的描述,上溯父母辈下到子孙辈,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到当下,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讲述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群里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清晨》里,追忆了母亲达玛拉与父亲林克,以及族长尼都萨满之间的故事,林克早逝后,因为氏族的习俗,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母亲和尼都萨满之间的情感只能被克制直至熄灭。童年的回忆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第二章《正午》里,因为日本人的到来,将一切都改变了,娜杰什卡因为害怕被日本人抓住,带着一双儿女逃走,为了找回他们,“我”在遇险的途中遇到了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我”的弟弟鲁尼娶了尼浩,尼浩接替了尼都萨满的身份成为族群的新萨满。在沉静舒缓、端庄雄浑中父辈们一一逝去,他们的爱恨情仇终结,“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已悄然开启。然而,疾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在第三章《黄昏》中展开,“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离开了,尼浩在成为萨满后救助他人,她的孩子也一个个逝去。氏族的主人们换成了子孙辈,她们在这片土地上面临了新的问题——去激流乡定居点生活。所有的章节中都在记录着各种各样的死亡,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这里。在生死面前,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一只灰色驯鹿的鹿崽曾代替姐姐列娜死去,列娜最终也在母驯鹿的身上冻死。这样的轮回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万物和谐共生。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