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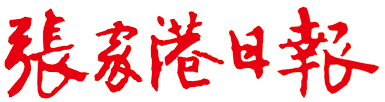
凉蝉一声,医心一寸
□郑显发
立秋凌晨四点,巷口的石阶先醒了。潮气从青砖缝里爬出来,像一条透明的蚯蚓,把夜里的闷热一寸寸拖走。卖豆浆的老周推开木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像给节气打了个招呼。他抬头,看见瓦檐上挂着的第一滴露珠——圆得像婴儿指甲,轻轻一抖,便跌进他掌心,凉得他打了个哆嗦。这哆嗦,便是秋天的第一声口令。
我跟着这声口令走进菜市。丝瓜摊前,大娘正掐断藤蔓,乳白的汁水溅到她指甲缝里,像给枯黄的手指戴上了一枚玉戒指。“立秋丝瓜赛人参,”她把一根弯似月牙的嫩瓜塞到我手里,“夜里咳,蒸半碗丝瓜蜂蜜水,一吃就好。”我点头,指尖触到瓜皮上细密的棱线,像摸到一条暗藏的药方。
午后,诊所的竹帘筛下细碎的光斑,落在老中医的脉枕上。他三指搭在卖鱼阿强的手腕,指甲缝里还沾着两片细鳞——那是清晨剖鱼时留下的。阿强咳得像漏风的老风箱,胸口起伏间,隐约飘出腥味。“燥邪伤肺,”老中医眯眼,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尾鲫鱼,“鱼鳞焙干研末,拌秋梨膏,连服三晚。”阿强揣着药方,临走时顺手把诊台上的薄荷糖含进嘴里,咂得一声脆响,像把咳嗽暂时咬碎。
傍晚,河堤上的风开始转性。柳条不再软塌塌地垂,而是绷成一张张弓,把蝉声射向远处。我蹲下身,拨开草丛,找到几棵马齿苋。马齿苋的叶片肥嘟嘟,掐断处渗出清酸的汁。小时候,母亲把马齿苋焯水凉拌,说能止泻。如今我采它,是为了治邻居小丫的痱子。她脖子后的红疹像撒了一把碎朱砂,痒得她直往树干上蹭。我把马齿苋捣成泥,敷在纱布上,叶片边缘的锯齿轻轻扎手,像提醒我:草木也有脾气。
夜里,月亮像被秋刀削过,薄得能透光。父亲坐在院中磨花椒。石磨“咯吱咯吱”,花椒壳裂开,麻香蹿上屋檐,惊飞一只宿鸟。他捏一小撮粉末,慢慢兑进温热的黄酒里——这是治关节痛的偏方。去年此时,他的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如今却能蹲下去拔葱。我接过酒盏,舌尖先尝到辣,再尝到麻,最后尝到了一点苦,像把一年的湿气都逼出来了。
蝉声渐歇,露水加重。我回到书桌前,摊开《岁时广记》,在“立秋”条目下补一行小字:丝瓜蜜、鱼鳞膏、马齿苋泥、花椒酒——这些草木与骨血的盟约,被节气轻轻撮合,像四味药材,煎成一碗人间烟火。窗外,最后一声蝉鸣跌落,像句号的墨点。我知道,等明日太阳升起,那滴跌进老周掌心的露珠,早已爬进某片叶脉,变成下一剂药引。
而医心与凉意,正一寸寸,长进每个人的骨头里。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